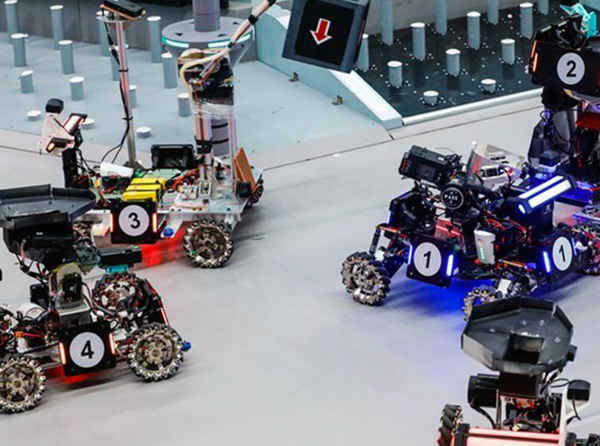张智言(中)上世纪80年代在陕西开始进行朱鹮的研究。
B
·寻鸟人
误入鸟群 雷达工程师与朱鹮结缘
在媒体关注四川朱鹮复兴进展的时候,有一位成都市民,也在持续关注着这个事件。相隔20余年听到四川将重建朱鹮种群的消息,对他来说,是件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也是一个有特殊缘分的“约定”。
“我不是学生物学的,但是很有趣,我最终和鸟类结缘。”2017年5月,成都市民张智言在看到本报关于朱鹮的报道后,提笔手写一封长信,邮寄到本报编辑部,“20多年前,陕西洋县那一批惊世复出的朱鹮,我还曾亲手抱过。”
张智言今年已经71岁,是个地道的成都人。1965年,他进入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学习雷达结构专业,毕业后被统一分配到兰州914厂工作,当时主攻电子工程仿生学。“我觉得电子技术与鸟类特征可以相结合,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对很多鸟类开展研究工作,其中包括朱鹮。”改革开放时期的经商浪潮里,张智言选择转身走进山林,“搞鸟类的研究是一个长线基础研究,短期是不会有任何的回报,但这是我的兴趣”。
洋县奇遇 辗转多地赴一个朱鹮约定
1930年,我国朱鹮曾见于14个省份。1957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洋县采获两只标本。1958年,在甘肃康县获得两只标本。1964年,在康县采到最后一只标本。此后,有关朱鹮消息彻底断绝。
“1981年,当听到科学家重新在陕西洋县发现了朱鹮的消息时,我觉得很振奋。”接受采访时,张智言从书房抱来厚厚一摞时间追溯到1990年的资料,在向甘肃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局和陕西林业保护局发出申请并获批后,张智言坐火车经陕西西安,转道洋县,走了几十里山路,最终到达洋县保护站三岔河观测点。他选择了“三岔河”中部的“老坟山”为自己的观测点。这一代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都是茂密的古青冈树,可供朱鹮营窝筑巢和繁衍生息。
等待2天后,在老坟山的一处小山头,朱鹮果然出现了。张智言架好三脚架,每日观察着鸟巢里的朱鹮。“当时正是繁殖季节,朱鹮两口子刚孵出3只小朱鹮。”但在日复一日的观察中,张智言发现,在3只幼鸟中发生了明显的抢食行为,其中2只小朱鹮已经出现了虚弱的情况。虽然这是动物界的自然法则,但眼看着珍贵的朱鹮很可能就此夭折两只,张智言坐不住了。

2017年3月13日,张智言向记者展示他上世纪80年代在陕西研究朱鹮时的报道。
小朱鹮垂危 电热炉和羽绒服救活幼鸟
张智言迅速向当地林业部门打报告,申请对幼鸟进行救助。得到同意后,请了2名当地人提着篮子爬上树,取下2只小鸟。“大朱鹮当时在天上盘旋,密切注视着我们的行动,但是朱鹮毕竟是天性胆小的鸟,最终营救行动还是比较顺利。”张智言刚救下这2只幼鸟,又得知另一个巢区送来了一只体弱的朱鹮,“3只鸟不能养在一起,要打架。幼鸟吃东西也是个问题。”
为了给朱鹮保温,张智言和当地工作人员一起,搞了2个1000瓦的电热炉放在朱鹮笼子旁边,还把自己的羽绒服脱下盖在笼子上。为了给朱鹮喂食,他们模拟野外环境,把手握成管状,把泥鳅剪成小段放入手里,让小朱鹮在自己手里吃东西。
7天时间之后,3只小朱鹮逐渐健壮起来。离开洋县之前,张智言抱着自己亲手救下的一只小朱鹮,留下了这张珍贵照片。
长期的知识积累和潜心研究后,张智言的多篇论文被国外学术期刊发表,他也被称为“业余鸟类研究工作者”。1986年6月,张智言收到加拿大举行的第19届国际鸟类会议的邀请书,由于当时经济原因没能参加。遗憾之余,组委会发来信件称,“你虽然未到会,但你对鸟类研究做出的贡献,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你是飞翔着的中国人。”
尽管后来没有机会再与朱鹮“相遇”,但张智言仍一直心系着朱鹮,期待朱鹮能重新出现在四川的天空。近期,朱鹮“第二代”顺利在川降生的消息让他激动万分,他与朱鹮的“约定”终于圆满了。
 四川新闻网首页
四川新闻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