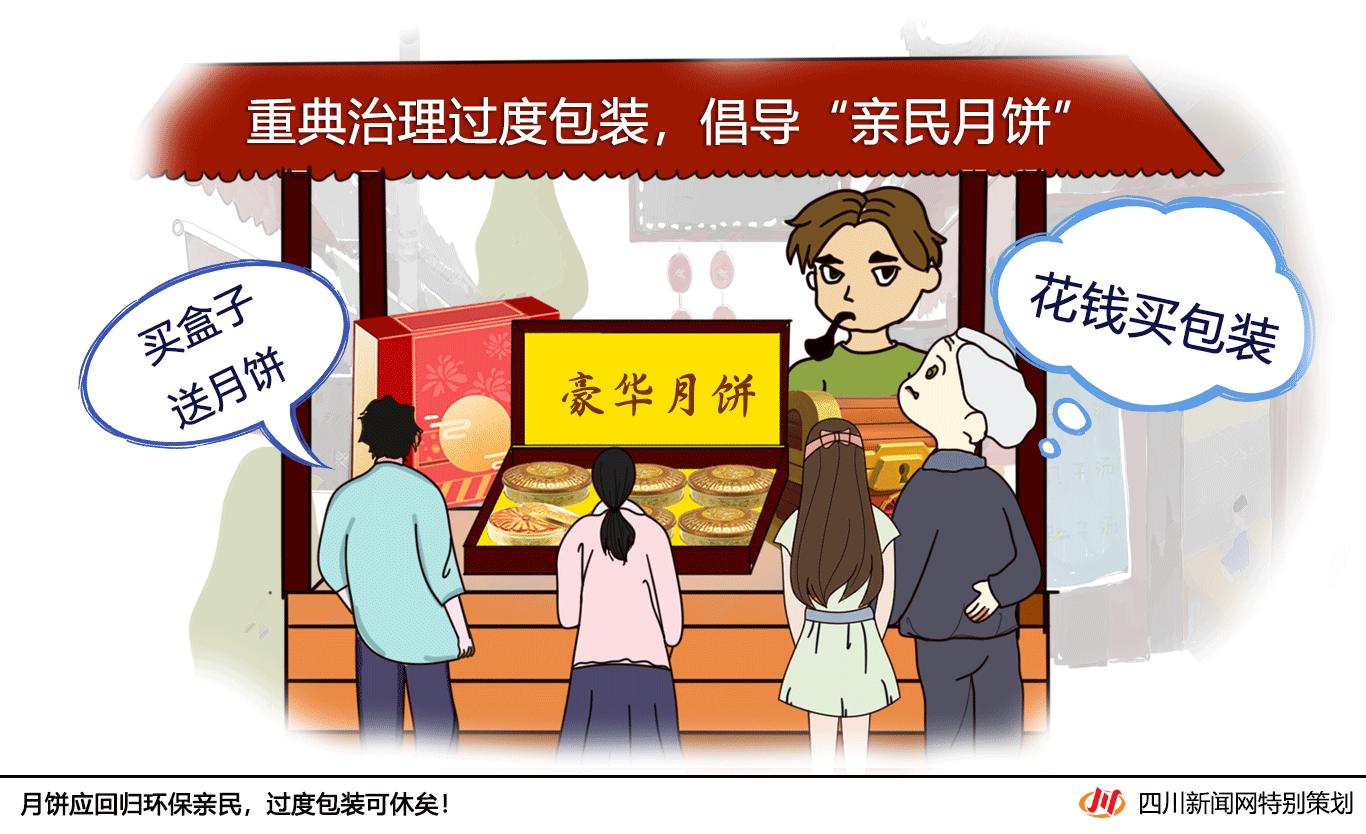杜先福
我是1993年从司法警察调到公安系统的。老实说,虽然同是警察,但因工作属性不同,从司法警察到公安民警,对我来说还是特别“新鲜”。当时我才39岁,正当壮年,身体状况也不错,从当兵到司法警察,先后20多年,见过坏人,尤其是在司法战线,见过数以千计的劳改劳教“坏人”,但是真的通过自己的手抓获的“坏人”,却一个也没有。到公安系统,第一念头就是时刻准备“抓坏人”。理由是,坏人被抓了,社会就稳定了,人们就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的平安,是党和国家检验执法机关的标准。抓坏人,则是警察义不容辞的天职。所以,在我认为,做警察,必须时刻不忘“抓坏人、保平安”。
然而,我走进公安队伍所做的第一件而且在我看来是千辛万苦的事情,却并不是“抓坏人”,而是,千里之外解救被拐妇女。
千辛万苦“白忙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问题十分突出,尤其西南三省则更为严重。1993年,市公安局成立了“打拐办”,但限于警力严重不足,一般情况,有被拐妇女儿童线索,基本上都是被拐妇女儿童所在辖区派出所出动警力前往解救。那年4月,我调宝台派出所。在市上进行了两个月“入警”培训,回到派出所正式上班第一天,所长钟建国就告诉说,你回来得正好,明天去山西忻州,解救被拐卖的一名妇女。
乍一听,我十分惊讶,怎么会派我?我倒不是要讲价钱,而是对于解救被拐妇女儿童,我毫无准备更是没有经验,根本不知道如何着手。只是从报刊杂志以及两个月学习培训,也知道一些解救工作的不易和艰难,我一个刚刚进派出所的“新人”,“出道”就是做解救,压力肯定很大。出于当“配角”的想法,我问:“哪些人去?”“就你自己。”
老天,“就你自己”! 我简直不敢想象“就你自己”。钟所说,本来不该派你,但是所里就四个民警,一个快60岁了,一个是女警,总不能让女警跑那么远吧!
我是无可推脱了。不过我确实心里没底,提出联防队员刘建林一同去。记不清具体日期,大概是7月几号,我和小刘踏上了去山西忻州的征程。为了节约经费,火车不能坐卧铺,就是特快也不能坐--特快票贵。车上,我问小刘对解救妇女儿童有什么“高见”,他比我还要“无知”,可以说什么都不懂。平时在派出所“帮忙”,也就是起个跑腿的作用--跟到民警跑跑腿,抓了“坏人”,看守着就行。加上他不善言谈,所以基本上掏不出什么“真货”。无奈,我只好自己设想了许多“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设想了许多“应对和解决办法”。
加上汽车,我们坐了两天两夜,到忻州已是第三天的下午四五点钟。赶紧去忻州地区公安处所属的忻州市公安局打拐办“报到”。按照我的原意,是立马出发,去被拐妇女所在的乡镇。“哪怎么行,去乡镇几十里嘞,今天肯定不行!”打拐办的民警老吕口气很硬。我们说害怕夜长梦多,走漏了风声就不好了。老吕却表示,没事儿没事儿,绝对走漏不了一丁点风声。
无奈,客听主人安排,只好歇下。为了赶时间,决定第二天早上四点出发,老吕说太早了,7点。好说歹说,确定早上6点在公安局门口等。
为了解救顺利,我把一路上诸多设想与老吕做了探索。老吕说我想得太多了,叫我们早点回旅馆,晚了用水可能恼火。回到旅馆已是晚上九点半,果然没水了,服务员说,忻州缺水,一般8点左右就不供水了,克服克服,明天早上再洗漱吧。
然而,我们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了,根本等不到供水。到了公安局,一等再等,那时候没有手机,连“BB机”也没有,无法联系,直到7点多钟老吕才骑了个三轮摩托从公安局出来,还说这是再三说好话刑警大队才“让出”来的,要不就得步行。
有摩托自然比步行好。当时我们派出所也只有一辆百病缠身的摩托,山西这样的穷地方,那时候能有三轮摩托,挺不错了。
那时候山西的乡村道路,一点不敢恭维。摩托车颠来簸去,几乎能把全身骨头抖散架,五脏六腑抖翻。上了路老吕似乎才记起,问我们吃了早饭没。怎么说呢,那么早,根本就没卖早餐的地方,哪去吃。其实我们也蠢,居然就没想到买点饼干什么的。无奈,只好克服克服了。
约莫行了二三十里以后,路没了--连可以跑摩托的路都没有了。问还有多远,老吕说可能走了一半的路程。沿着黄河走,可能要两三个小时,边走边看,有方便的船,就坐船。
常言说,慢船跑死马。有船当然更好。说来也是运气,居然就有一艘运砂船,老吕喊了几声,船就靠了岸。上去,愿意坐,可以坐在砂子上。不过砂子是湿的,不敢坐。
记不清当时心里都想了些什么,只记得那天去到那个村子已是下午一点多钟。肚子饿得好像所有预存的食物都不存在了。虽然又饥又渴,但是第一意念还是马上去到那个被拐女子的“家”。那个村子在黄河边的半山上,从河边上到半山,实在是无法形容当时是怎样爬上去的。比我小10来岁的刘建林后来说,他根本不晓得自己还能走动几步,如果不是我在前边带头,他绝对是不愿再走。
怀着极大希望,爬上半山的村子,找到村社干部,带到那家村民家,却是“铁将军”把门。村社干部说,这家人一直就没人在家,早就出外打工去了。
我虽然不是侦查兵出身,但多少还是会观察。这家院子里还有几只鸡,并且这些鸡不像是别人家的。再看屋檐下的灶台,虽然灶台上空空如也,但是却比较干净,不像久不做饭落满灰尘的那种状况。我伸手掏了一把灶孔里的余灰,居然还略略的有点烫手--我想,肯定中午还做了午饭,只是现在没人在家了。
我不知道哪里出了纰漏,当然也不好怀疑老吕。我没有动声色,村长叫去他家吃午饭。肚子是大事,无奈,那就先填肚子。
午饭是豆腐,其他就是啤酒,除了豆腐和啤酒,再没别的。可见当年这里人们的生活--真的不敢恭维。
吃饭过程中,村干部一再声称那家村民举家出去打工了,家里绝对没人。村长表示,只要那家人回来,就向公安局报告,“放心,绝对不会包庇!”村长信誓旦旦。
我相信村长说话算话,毕竟,村长已50多岁,并不是三岁小孩。
吃了午饭,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回去可不同于来时有顺便的砂船,从村里到摩托停放地20多里得步行。沿着黄河岸边走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坐上足以令人散架的摩托,回到城里已是晚上8点多钟,吃了晚饭再到旅馆,娘的,又没水了,因为确实疲劳,也不想另去找水,只好继续克服,倒头就睡。
睡到凌晨三点多钟,我突然醒来,心里老是觉得不踏实。这是来解救妇女的,可是现在却“八”字还没一撇,回去怎么交差。村长说等那家人回来就报告,可是那家人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心里老觉得那家人没有走远,说不定这天晚上就已回到家里。“马上出发,去村上!”我拍拍小刘的屁股,叫他起床。
“杜公安,你是要我的命哦!”小刘明白我的意思后,十分恼火,“半夜三更,人生地不熟,几十里,怎么去,不是要命吗!”
“这个算什么,部队三线建设,有时候为了赶工期,十天半月吃住在工地,那才叫要命!”我说,如果你实在感到恼火,就我自己去。其实我这是激将他。果然,他无可奈何,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跟着我出了旅馆。
有必要补充的是,因为时间不凑巧,赶不上旅馆供水,于是给服务员打了招呼,给留一瓶开水。昨晚回到旅馆,开水太烫,没办法用来洗漱,就把水瓶盖揭开了,凉起预备第二天早上使用。出发时水还是温热的,灌进军用水壶正好。在部队养成的习惯,不管走哪里,必带军用水壶。转业二十年了,每当出差也总是带上军用水壶,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出门时小刘说今天又得唱“饿龙岗”了。我说放心,乡村公路尽头那地方有个推销店,赶到那里可能天就亮了,买点粑粑饼饼没问题。
夜里步行,心无旁骛,走得就快,到那推销店时,天还麻乎乎的看不清东西。敲门说要买东西,主人家大概害怕我们是坏人,高矮不开门。我们等不起,决定先赶路。我心想,今天真的又要唱“饿龙岗”。小刘虽然心有不满,但也奈我不何!
紧赶快赶,赶到村上也已9点多钟。担心目标太大,我们不敢大模大样地走大路。因为不熟悉村里情况,找不到该走哪里,“鬼鬼祟祟”凭着昨天的印象,大致朝着那家人家走去。因为没带便衣,我是有公安标志的警服,小刘也是“光板”警服,所以仍然很“打眼”。一路走,一路总有村民异样的眼光。走着,居然有村民说又来啦?显然那村民昨天看见过我们。我心想,既然已经认出了我们,何不请他带个路。那人却笑笑,说不不不。我们也不好勉强,继续往前走,偶尔回头,那村民还在那里笑,样子很奇怪。我想,今天肯定又是白跑。
果然,等我们找到那个村民家,仍然是“铁将军”把门。灶台上还是昨天的老样子。我仔细观察,灶孔里还是我昨天探查过的状况,看样子这家人昨天并没有回来。
带着无限失望,我们找到村长,意思是想麻烦他“认真对待”。没想到刚一见面,村长就对我们好一顿“洗涮”,说我们这是对他不信任,也是对村里人不信任。他说,昨天我们走后,他就布置了村民注意观察那家人的动向,只要有消息就向村里报告。还说,他也安排了人去找那家人的亲戚,动员那家人把女娃送回来,免得弄得村里鸡犬不宁。最后说,我们这一折腾,肯定“打草惊蛇”了,那家人肯定会躲得更远。
村长这一顿“洗涮”天衣无缝、非常有道理,但是我却总感觉背后有名堂。只是,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们不能大明其白地指出来,指出来“得罪了”人家,恐怕连我和小刘都走不了路脱不了身。
万般无奈,我们只好一再表示感谢,然后在村里推销店买了几个炕饼,匆匆离开了村子。
坐在一个山坳上,我们开始早餐。其实那时候已经上午11点多钟。费了莫大的劲,却毫无所获,我心里非常难过,既难过于那名妇女可能遭遇的种种凌辱与不幸,也难过于毫无所获回去后不知如何交差。炕饼本就干,加上心里难过,那炕饼就十分难以下咽。水还不能“敞开喝”,两个人就那一壶水。那个时候,真就想起战争年代先烈们的艰苦与艰难,自己这点儿艰难真他妈算不得什么!
因此,炕饼还是艰难地下咽,水则“省到省到”地喝。感觉肚子里已经有货了,我又来了精神。我说,我们回去,爬到山上看得见整个村子的地方观察观察,说不定能有收获。
说实话,我心里为回去交不到差而恼火,一再希望有什么奇迹。尤其是想到那妇女可能遭受什么凌辱和苦难,心里就十分不是滋味。
小刘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毕竟我是正式公安,这次出差,他必须听我的。我这人就这点不好,做事总是很固执。
“鬼鬼祟祟”大概爬了半个多小时,爬到一个制高点,基本看得到村子的全貌。于是,我们眼巴巴地看着村子,希望出现“奇迹”。然而整个村子十分安静,毫无奇迹发生的迹象。我耐着性子,小刘也耐着性子,等待和企盼奇迹的感受至今还五味杂陈,说不清应该怎样形容。
最后,大约下午四点多钟了,实在等不到什么奇迹了,小刘以一句话不说表达着心里的恼火,我也觉得再这样熬下去不可能有收获,只好非常失望地回城去。到城里已是晚上十点钟,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夜宵店,记得我们要了两个凉菜,四瓶啤酒。吃完回到旅馆,自然又是没水,自然又克服了。就这样,应该是好几天都没洗漱了。
因为头天辛苦疲劳,第二天就起得比较晚,起床时旅馆又已经停止供水,于是又“克服”。吃早饭时就和小刘商量接下来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是给所里打个电话,汇报这边的情况,看是继续等候村上的情况报告、还是回去等候消息。电话那头说,那个女子的堂哥正在忻州找我们,说是昨天找了一天,不知我们去哪里了,现在那哥子还在公安局。于是,我们赶紧去公安局,结局令我们哭笑不得。
原来,那哥子多年前就到山西打工,煤矿挖煤。后来把自己的堂妹叫去矿山做饭,堂妹和一个山西本地矿工好上了,去了那个矿工家。这事儿遭到女子家人的极力反对,到公安局控告那哥子拐卖妇女,还到有关部门上访,闹得沸沸扬扬,非要那女子回家不可。
事情闹到宝台派出所,女子家人已经多次到宝台派出所要求解救,并且给派出所交了2000元经费,这不,就有了这次到忻州的解救行动。
然而,当我们在忻州艰苦忙碌时,女子却已赶回四川家里,并且还有那个矿工--他们愿意结婚,到四川就是来办结婚证。于是,电话打给还在山西煤矿打工的那所谓拐卖妇女的哥子,那哥子如释重负,赶紧来告诉我们不要再解救了。
一场白忙,真是哭笑不得。
其实,公安工作,“白忙”的活儿数不胜数,只是一般人根本不了解罢了。
那次回到家,老婆把我的军用挎包里没有洗过的换洗衣裤掏出来,顿时就给扔进了厕所,叫我自己洗,并且赶快洗--换下来的衣裤,在挎包里沤得发臭,不怕笑话,真的是臭不可闻!
并非惊心动魄抓“坏人”
前文说了千辛万苦的“白忙活”,接着就来说说我抓“坏人”的二三事。关于我抓坏人的故事,并不怎么惊心动魄,但却有几分精彩。
这里所指“坏人”,严格地说是指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却又可能是犯了罪的人,在公安这个环节称为犯罪嫌疑人,人们口头习惯称“坏人”。
当年宝台派出所没有轿车,仅有一辆三轮摩托,据说还是刑警大队不要了,宝台派出所拿去修了修,换了些部件,勉强可以跑。摩托车因为内脏有毛病,经常“闹情绪”,跑到跑到就断气。很多时候还得几个人推回所里。所以一般情况,我愿意骑自己的自行车。
基层民警,以保一方平安为天职。在没有轿车、而且警力也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所里治安巡逻全靠那辆三轮摩托。当年最让人头痛的是车匪路霸,而宝台派出所辖区最容易发生车匪抢劫的路段就是资(阳)资(中)路的拱城铺、资(阳)乐(至)路的蜈蚣桥这两处的上坡路段,因而派出所巡逻的路段也主要就在这两处来回奔波。
当年,碎石土路,颠簸不说,仅仅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水四溅就够人难受了。我刚刚进入公安队伍,比起所长和另一位老同志凌宗明都要年轻,加上我自己也想挣表现,因此上路巡逻便是家常便饭。所里三名联防队员,他们都会驾驶摩托,只有我不会,因而他们可以轮流上路,唯独我是连轴转,因而每天巡逻过后,总是鼻子眼睛全是灰尘,基本不成人形。虽然这样,但却并没多少怨言,因为那个时候(直到今天也一样)几乎大家都是一个念头:干都干到这一行了,咬起牙巴也得干!
日复一日的日常艰辛并没什么可以炫耀,值得炫耀的是,当公安必须得抓几个坏人,不抓几个坏人,公安就算白当了。
我第一次抓“坏人”真的不算惊心动魄,但确实有几分精彩。记得那是一个下午三点多钟,我去看守所送一份调查补充材料,一个电话打到看守所,说拱城铺发生车匪抢劫,叫我直接赶去现场。我毫不犹豫,骑着自行车立马就往拱城铺去。也不知道哪来的干劲,居然蛇行着奔上了拱城铺那个大坡(事后多次试图骑上那个坡却总是没有成功)。我到时所里几名联防队员刚刚到,说没什么车匪,就是几个社会混混到学校敲诈、骚扰,很多次了,报了案却没人重视,所以这次就报有车匪。不过还是来迟了,几个混混已经跑上山不见了踪影。我问,跑了多久?几个联防说,刚才还看见在翻山,最多就在山背后。我心想,必须得把那些混混“端了”,给学校一分安宁!
“你们几个后头来,我跑前头,追!”我说完拔脚就追。跑了几十米,觉得脚上的皮鞋太碍事,一边跑一边甩掉鞋子,喊后边的人帮我把鞋子捡到。脚上轻巧了,虽然是上坡,自己感觉还是在飞--不是吹牛,在部队时团里遴选长跑运动员,5公里我曾经跑到全团第三名。
当我跑到山顶时,看见四五个娃儿正在下山。他们看见我,扯开趟子就跑。我也不喊“站住”,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是下山,简直可以用“飞”来形容。很快我就追到了山下,几个娃儿正在过田坎。我追上后边那个跑得慢的,就势一拉,那娃儿立马滚到稻田里。我顾不上这个娃儿,直接冲到最前边,返身挡住还有四个娃儿的去路。当时我手上仅有一幅手铐,挥舞着叫这些娃儿:“老实点,趴到地上!”不是吹牛,我的嗓门很大,声音很高,几个娃儿被我的气势所威慑,真就乖乖趴在田埂上不敢动。几个联防队员赶来时,我都已经缓过气来,呼吸已经均匀了。
后来,这几个未成年人(最大17岁,最小的15岁)除一人治安拘留三天,其余均教育写了保证交家长领走。从那以后,学校就再没受到骚扰了。记得学校还给派出所写了感谢信,信里特别提到了我打光脚追击的事情。
说起来,这次打光脚追击并不算什么,而另一次“打光脚”那真的才叫“刺激”。
记得是某天中午,群众举报,宝台派出所列为“逃犯”的杨某现身火车站后边的配件厂某家属区的亲戚家。一名联防队员专门到我家,说那名“逃犯”已是几次进出派出所,大家彼此都认识,唯独我新到宝台所,那人不认识我,所以要我穿便衣先去辨认。当时我正在吃午饭,二话没说,抓了件便衣就出门。出门时家人不无担心地说了句:“小心点哈!”我“嗯”了一声,那一声已经是在下楼的楼梯上。
还是那辆破三轮摩托,到了火车站,没敢把车子骑到配件厂那个小区,我在前,联防在后,跑步去了小区。按照联防的描述,“逃犯”的亲戚在巷子里第几个门,“逃犯”脸很宽,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力气很大,认准了不要轻易动他,怕他身上有凶器,尤其怕他乱来伤到人。当我走进巷子,默默地数到第几个门时,门口就坐着一个宽脸盘的人,不用猜我就断定那就是“逃犯”。那人十分敏感,见了生人就像“惊弓之鸟”,居然起身就跑。我喊了一声:“他跑了!”意思是告诉后边的联防赶快追来。我也没想那家伙身上是否有凶器,他在前边逃,我也拔腿追。追了不远就是厂区铁路,看样子那家伙二十多岁,腿脚还行,跑得挺麻溜,眼看就拉开了距离。
“娘的,老子拼了!”心想决不能让这家伙在我眼皮底下逃掉。我觉得皮鞋碍事,又像前次一样,边跑边甩掉鞋子,光起脚板就追,根本顾不得铁道上的碎石道渣是不是扎脚。因为脚上没有什么重量,跑得就快,很快就追上那家伙。我仗着手里有手铐,一边挥舞一边叫喊“站住站住”。那家伙情知跑不脱了,站住并回过头来,说是不跑了。我就喊:“就地趴下!”他说:“道渣不好趴。”我不由他分说,一再叫他“趴下”,那家伙只好趴下。我叫他把手反背到背后,那家伙不得不反背了手。等我把那家伙铐好了,联防才跑来,当然也给我把鞋子捡了来。
后来,我跑出血的脚底至少十天没敢洗,怕沾水化脓。这个事儿,被派出所新来的指导员写了个新闻登了出来,狠狠地表扬了我赤脚追逃犯。
其实,两次赤脚追击,对于我来说都觉得是小菜一碟,就像是逮了几条小鱼甚至是虾虾,值不得炫耀,我心想,有机会,我得弄条大鱼。干公安,不抓住几个像样的犯罪分子,真不值得炫耀。
不久,机会真就来了。
一天夜里,所里举行“收网行动”--抓捕车匪路霸。这是经过一些时间的摸排确定的几名车匪,这天晚上进行收网。收网行动还有刑警大队配合,分了三个小组同时展开。我所在的小组是到拱城铺山坡路段一条小公路旁的民房抓捕一名嫌疑人。为了不暴露,大家都是步行。到了那条小路,进行分工,居然把我分到公路边设伏,说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行动,没经验,担心我弄出响声影响抓捕。
叫我设伏,就是如果有人往这个方向逃跑,就叫我开枪,因而把所里唯一的一支五四式手枪给了我。记得带队的是刑警队一名民警,他告诫我,看到有人,先要喊话,问清楚是不是自己人,不要乱整哈!我说,放心,不是万不得已,我不会开枪!
设伏就我一个人,我当过兵,受过军事训练,我不可能立撑撑地站在某个地方。我在公路边的草丛里隐蔽起来,臆想着如果有逃犯跑出来,我该怎么处置,是扑上去,还是先开枪,反反复复想了许多,终于有几个人影出现,看那从容的形景,我就知道我“没戏了”。等到人影清晰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嫌疑人”已被抓住,民警们没有喜悦高歌,倒也说说笑笑。毕竟,没有白费功夫。
不过我心里却十分“不了然”,因为这样的抓捕,于我是毫无功劳可言。我想,有机会,我一定要亲自抓条可以“显摆”的大鱼!
常言说,机会总是会赏赐给有思想准备的人。这不,没几天,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刚刚上班的时候,我第一个到所里,自行车还没停住,就有早已等在派出所的群众举报说,派出所要找的B回家来了,赶快去抓。B是宝台镇协议村人,车匪路霸团伙中的二号人物,身上有多起抢劫案件,因其最近在外打工,同伙被抓后一直没有动他。可能认为同伙没有供出他,所以就回来了。得此信息,我很激动,决定立马就出发。不过临走前我还是请那前来举报的群众稍等一下,等派出所其他同志来了,告诉他们,我已到村上去了,叫他们随后赶来接应。
我骑着自行车刚刚出派出所院子,所长上班来了。我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叫他们随后赶快来。所长也是轻描淡写:“好的,我叫他们马上来!”
那个“他们”当然是指所里其他民警和联防。记得自行车骑出去十几二十米了,所长才在背后不轻不重地喊了一声:“注意安全哈!”我连“嗯”一声都没有,因为没有必要,即使“嗯”了,所长也不一定听得见。
从宝台派出所出门就是资乐公路,然后就是蜈蚣桥、马站到协议村,路程不远,记不清当时速度有多快,感觉就像撒了一泡尿的功夫就到了协议村。因为此前摸底时已经掌握了B的住处,自行车撂在公路边,直奔B的住处。但是没人,打听,说半小时前看见他背了个鱼篓到沱江河边去了。B爱抓螃蟹,一定是到河边抓螃蟹去了。
当时,根本没有想等到其他民警和联防赶来了一起去河边,也没法告诉村民说我去河边了。我得随机应变,立马去河边,以免走漏风声让他跑了。
我对去河边的路径并不熟悉,但是大方向还是知道。最初我像若无其事--怕的是太匆忙引起村民疑惑而打草惊蛇--到了没有人迹的地方,我立马朝着河边撒腿飞跑。很快我就看见河边有个人影,人影虽然模糊,但我猜想那一定是B,因为除了他,河边并无别的人影。
为了不惊动,我没有大摇大摆,而是隐蔽着接近,直到实在不能隐蔽了才向河滩走去。从隐蔽的地方大概要行进二三十米河滩,根本没有遮拦,因为我穿着警服,所以当我刚刚现身就引起了B的注意。我发现B看见我的时候至少愣了十秒,接着他拔脚就跑。他这一跑,毫无疑问应是心里有鬼,我哪里能让他跑了呢!
河滩上跑步,穿鞋子肯定不行,所以我又毫不犹豫,立马甩掉鞋子,撒腿就追。B个子高大,身体强壮,如果单对单,我很可能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没有拼命追,而是悠悠缓缓,意在消耗他的体力--我很自信,自信我的耐力会比他好。
B在前边跑,好几次都踏进了水里。说实话,我的游泳水平很差,儿时在牛滚凼“狗刨沙”可以整几下,堰塘里也可以捏到鼻子翻几翻,但是沱江河里还从没体验过,B在沱江边长大,他要跳进河里,我真还没法。
不过,那个时候,他真的跳河,我想,我也会毫不犹豫跳下去。可以理解,许许多多的英雄,尤其我们公安战线的英烈,几乎每天都有牺牲,许多人的牺牲,都是关键时刻的“毫不犹豫”,如果一旦犹豫,可能就不会是英雄了。
事后同事说,那天B要是真的跳河,真还拿他没法。我说,他娃真要跳河,老子不得打半个“嗯腾”--也即不会有半点犹豫,一定追到河里,大不了就是“光荣”了而已!
B在前边跑,从他踏进水里却不跳河的状况来看,我猜想他也不会游泳,所以我在后边“赌”他,“有本事你跳河,跳河老子就砸死你!”--河滩上卵石很多,他要跳河,绝对砸他,砸晕了我再下水弄他!
其实,如果有枪,我肯定会鸣枪示警,遗憾所里仅有的一支五四式手枪,通常都是所长或指导员轮流使用,我那天仅有手铐。
跑了不很远,B竟跑不动了,弯下腰直是喘大气。我担心他借机捡起卵石砸我,所以没有立即接近他,而是挥舞手中的手铐,叫他趴下。他说他“不跑了,绝对不跑了”。我口气非常生硬,一再叫他趴下。他磨磨蹭蹭,打算趴下时,我见他面前有不少卵石,于是我立即命他面朝河边趴下--河边全是泥沙,而且又是背朝我,便于铐。接下来就简单了--反手铐起,拖他起身,押解到公路上,所里民警才刚刚赶来。
经审理,B单独或伙同他人一起作案,抢劫13起,之后即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五人团伙覆灭后,宝台辖区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车匪路霸的案件了。
(来源:“我和祖国共成长”优秀文艺作品评审委员会)
 四川新闻网首页
四川新闻网首页